2022年3月,春天剛剛回到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的院子里,但院子里的師生們,卻不會再見到張子儀老先生的身影了,那位風度翩翩的長者,那位為中國現代畜牧業奠定重要基礎、讓無數人實現了肉食自由的科學家,過去每次走在這個院子里,總會牽動很多人的目光。
3月31日,張子儀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享年98歲。悼文稱,這位中國動物營養與飼料科學的開拓者和主要奠基人、中國飼料工業及現代養殖業的主要鋪路人,“牽頭創建了全國統一的飼料樣品采集方案,制定了《暫行飼料分析方法》,并于1959年出版了我國第一部《國產飼料營養成分含量表》,為我國飼料工業和畜牧科技發展做出了里程碑式貢獻。”

回國,只為了人生無悔
1925年,張子儀出生于山西臨猗縣一個書香世家,從小養成深厚國學功底的他,卻選擇了科學救國。于1941年9月東渡日本求學,隨后考入京都大學學習農學,1948年,本科畢業后,繼續攻讀動物營養學。
上學時的張子儀,就顯出了農學中卓越的天賦,當時,日本滋賀縣出現耕牛“異嗜厭食癥”,每到冬季,耕牛往往少食而消瘦,這一癥狀一度被認為是“氟中毒”的表現,難以治愈。當時,張子儀的導師讓他去做環境營養學分析,他遍采水土草料樣品,歷時一年多,分析發現并非“氟中毒”,而是當地環境中普遍缺乏一種元素“鈷”,隨后配制劑,使大批耕牛康復。在當時,反芻動物的鈷缺乏癥,在整個國際上都屬前沿性課題,在澳大利亞、美國等均有病例,卻缺乏研究。張子儀的研究,不僅解決了鈷缺乏癥的問題,也開啟了動物營養學中,微量元素營養的研究大門。
張子儀在日本攻讀學位時,正值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人才奇缺。已經在日本小有名聲的張子儀,決定回國。對于這個決定,張子儀解釋,“從個人得失出發,繼續留在國外,不過平添個‘博士’頭銜,社會地位、個人生活條件會好一點,但不可能有更大作為。”
張子儀把回國當作人生最重要的起點,“重新自我設計,以慰或冤死敵獄或捐軀疆場的千百萬同齡人在天之靈,此乃人生無悔之起步。”
奠基,查遍每一種飼料
張子儀回國后,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耕牛冬季飼草不足的問題,為此,他在山東、山西、河南等地,向農戶傳授和推廣玉米收獲后的秸稈青儲技術,讓耕牛能夠在冬春季青黃不接時,也有飼草可吃。在1954年春,各地青儲窖開啟,青儲無一失敗。
20世紀50年代,豬飼料主要依靠青、粗飼料,人們仍舊用千百年來的傳統方法喂豬。為此,張子儀主持了國產飼料資源普查及開發利用的項目,并于1958年首次在全國統一了飼料樣品采集、制備的規范,制定了《暫行飼料分析方法》,第二年,又出版了我國第一部《國產飼料營養成分表》。
“在全國各地,每一種動物的飼料都有百十種,如何才能精準地分析出各種飼料的營養成分,是一個大功夫,也是畜禽科學飼養的基礎工作。”張子儀的學生、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科院北京畜牧獸醫所研究員侯水生說。
張子儀的研究,開啟了中國飼料營養科學的大門,成為科學養殖最重要的基礎之一。
1969年后,張子儀隨北京畜牧獸醫所離京,輾轉至柴達木盆地,在當地建立科學養豬示范豬場,并在9年中整理了諸多原始資料,用算盤、巴羅表等手段,整理、勘校、篩選印發了《國產飼料營養成分表》。
對張子儀來說,柴達木盆地的9年,是最重要的人生經歷之一,在那里,他遇到過成群的蚊蟲,被蚊蟲咬得傷痕累累的孩子,也遇到過借宿陌生牧民家時,牧民為防犬傷客為他通宵守夜的經歷。在張子儀的自述中,這一段經歷記述尤詳,“牧歌中之藍天、白云,駿馬奔馳,竟是蚊蟲之天下……高歌草原者,可曾領略人間還有這等疾苦?萍水相逢,非親非故,得此一夜親情,深感人世間仍有‘世外桃源’。”
引領,建立科學的方法
1979年,年逾半百的張子儀回到北京,重新開始飼料營養的研究。不久之后的1983年,剛剛大學畢業的侯水生,被分配到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工作,他也是在那時候遇到張子儀的。
彼時,張子儀正主持一項“營養物質消化吸收”的研究,侯水生回憶,要測定營養物質的消化率,比如說一頭豬,吃了多少飼料,消化了多少,又有多少沒有消化吸收,排出體外了。一般情況下,這樣的研究,都是通過飼養動物,預先分析計算飼料中的營養物質,然后再收集排泄物,如糞便、尿等,分析計算排泄物中的營養物質,兩者對比,可以得到消化吸收的數據。但這是一項極其繁雜的工作,要分析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種飼料,一百年也做不完。
為此,張子儀創建了一種體外消化的實驗,采集動物體內的消化液,分析成分,同時在外部裝置中和飼料混合,觀察反應,分析消化情況。
“動物消化有兩部分,一部分是物理消化,比如牙齒的研磨,禽類通過胃部收縮壓碎食物等;一部分是化學消化,就是通過消化液來消化吸收。”侯水生介紹,張子儀創造的體外消化實驗模式,大大加速了基礎數據的收集,建立了一整套消化模式,效果非常好。而且,張子儀還主持建設了世界上第一套人工消化器,如今還是北京畜牧獸醫所一項標志性的成果。“僅這一項技術,對我國飼料的工業化、標準化就至關重要。”
張子儀的另一位學生孫德林,也記得這段經歷。1980年,他剛剛上大學,寒假時,老師布置了一個任務,要求畜牧專業的學生,放假回來后,帶回當地的玉米、豆粕。后來才知道,這是張子儀主持的科研活動。
張子儀的工作遠不止此,他還主持或參加完成了《中國飼料工業標準體系表》《飼料工業原料標準》《飼料工業衛生標準》《飼料添加劑》標準等。同時,還主持了“中國飼料數據庫”的建設,實現了飼料營養研究成果信息的現代化管理。
幸福,來自肉食的感觸
在北京畜牧獸醫所,出版《中國飼料成分營養價值表》是一個傳統項目,到2020年,這個《價值表》已經更新到第30版。它的第一版,就是張子儀主持編制的,于1989年發布。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從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人的飯桌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幾何時,吃肉還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大多數人只有在過年的時候才能吃一頓肉,蛋和奶,同樣是日常生活中的“奢侈品”。但在今天,不管是肉,還是蛋、奶等,早已變成了普通不過的“消費品”,14億人也實現了肉蛋奶的“消費自由”。數據顯示,從1980年到2021年,我國人均肉類產量增加了416%,這一切,都有賴于養殖業的現代化,而其中,飼料科學無疑是基礎之一。
“中國的農業向何處去?”這是張子儀曾經提出過的問題,在解決了吃飯問題之后,生態成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在動物營養學中,同樣面臨著生態問題。對此,做水禽育種的侯水生,曾經在環境問題中,得到過張子儀的很多指導。侯水生說,“我研究家禽,張先生給我提出過很多建議,比如動物福利的問題,他經常告訴我們,養殖動物,要給它一個良好的環境,動物才能更好地生長發育,發揮出自身的潛力。后來,我們遇到過很多問題,比如鴨子要戲水,這是它的天性,也是它的需求。但我國每年出欄50億只鴨子,都給戲水,對水資源、對環境造成的壓力太大了。怎么辦呢?我們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現在我們育成的鴨子,在旱養的情況下也能非常好地發育和生長。這些,和張先生多年來的潛移默化是有關系的。”
育人,留下寶貴的精神
除了是一位科學家,張子儀還是一位嚴格的老師、一個慈祥的長者。
侯水生回憶說,“張先生對科研非常嚴謹,每一個實驗,都要求反復,每一個值得思考的點,每一個特殊的數據,都要追根究底。但同時,在對科學的態度上,又是開放而包容的。”
在畜牧科研的領域,張子儀是第一代科學家,而侯水生算是第三代,“我比張先生小30多歲,是真正的晚輩,但在科研中,張先生從不忽視晚輩的意見,尤其是面對科學問題,常常和晚輩平等地討論,而不是說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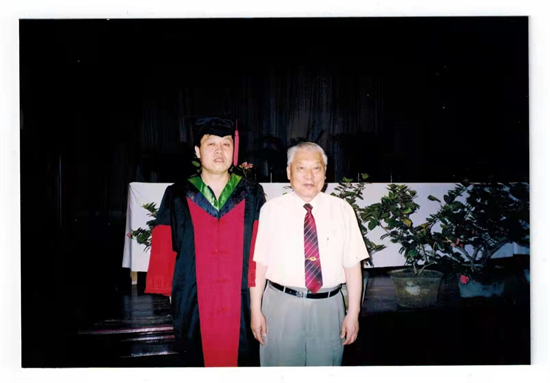
侯水生清楚地記得,他曾對張子儀的一個“動物因缺乏能量而采食”的觀點質疑,兩個人各持論點,各有論據,爭論了很久。“張先生經常講一個標準砝碼的故事,世界上最標準的1KG砝碼,在不同的環境中,其質量可能會有極其微小的差距,科學也是這樣,萬物沒有絕對,正因為如此,科學才值得不斷去探索。”
生活中張子儀,又是一位極具風度的長者。侯水生說,“只要是正式的場合,開會、學術討論等,張先生永遠都是西服、領帶,風度翩翩。”
張子儀的另一位弟子陶秀萍也講述了很多張子儀的故事,“張先生對學術要求很嚴格,我攻讀博士學位第三年,他認為我作為動物營養與飼養科學專業環境與營養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前期研究側重于環境控制,環境生理方面還需要加強,希望我延期畢業,就問我‘延遲半年畢業行嗎?’。還有一次,我將博士論文中一部分研究內容撰寫了一篇英文小論文,順理成章把張先生列為通訊作者,但張先生認為他在那篇小論文中的貢獻不夠多,不適合署名。可見他對學術的嚴謹。”
陶秀萍說,“每年教師節,我都會去看望張先生,每一次,張先生會準備一個話題,這也是他的習慣,讓我收獲滿滿。張先生還會親自做牛肉面,自己選肉,燉好幾個小時,等學生們來了以后一起吃。”
2021年教師節,陶秀萍最后一次見到張子儀,那一回,張子儀準備的話題是“寬容”,還送她一對鎮尺,上刻著“大海有真能容之度,明月以不常滿為心”。
或許,這也是張子儀對自己的要求,這位為中國飼料科學奠定基礎的學者,也是培養了無數科學家的教師,卻在他的自述中格外謙虛,他說“少年十五二十時,曾懷‘步行奪得胡馬騎’之志,欲‘按圖索驥’,謀科學包裹之策……耄耋行列……唯冀蠟炬成灰,尤可護花……”







